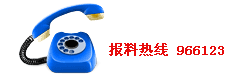■ 周华诚
这家叫南巷的咖啡馆藏在贵阳的某条小巷子里,由一座老民房改造而成。主人是位姑娘家,她说自己以前在电视台工作,现在出来开咖啡馆,主要是因为自由。自由的灵魂都在路上,不是为了目的地,而是在于一路的风景。这样说话的时候,她给我递上菜单,我一眼就看到了一行字:折耳根咖啡。
我其实能接受折耳根的味道。我连木姜子都喜欢。我家楼下有一家遵义羊肉粉店,偶尔去吃一碗羊杂粉。后来吃得多了,就习惯了他家的味道,原来是加了木姜子油。折耳根呢,我也在贵州吃了很多回,有一年去普安访茶,在偏僻小镇上吃饭,店家腌了一脸盆的折耳根,跟辣椒腌在一起。我吃过以后,觉得好。可是折耳根在杭州就很少见,菜场里几乎没有,在小吃店里更无从寻觅。超市里倒是有的,一般人也不太去买它。
折耳根的特别,在于它的气味有点怪,很多人觉得难接受。折耳根还有个别名,鱼腥草。我觉得名不符实,它和鱼的腥臭之味其实搭不上边。不过,世上的事物就是这样,有人嫌恶至极,也有人喜欢得不得了。萝卜青菜,各有所爱。有的人觉得折耳根难闻,偏偏也有人喜欢它,云贵人民大概普遍是喜欢的。据说贵州人民抵御感冒病毒的能力,要比别的地方的人强一些,原因一是他们爱吃酸汤,二是他们爱吃折耳根。这一说法,我不知道有没有学术支撑,但是折耳根本身就有清热降火的作用,此言应不虚。
在贵州,折耳根是常见之物。在路边吃米粉的店里,一般都会有折耳根供食客自由取用,就好像在北方吃面,店家一定会把一大盆生蒜妥妥地安排在桌上。跟生蒜相比,折耳根的气息还算温柔的。脆哨跟折耳根,都是米粉的绝配。我在别的地方,很少看到脆哨,一开始望文生义,一时茫然,不明白是个什么。街上有罗家脆哨、徐家脆哨、王家脆哨之类,招牌上的字一律做得巨大,店名一律冠以姓氏,显得根正苗红,仿佛老板在拍着胸脯,“不好吃我不姓罗”,“不好吃我不姓徐”,很有说服力。我还凑近去看脆哨,原来就是肥瘦比例合适的肉块放在油锅里炸,炸得脆香时捞出来,就是脆哨。“哨”的意思,就是“哨子”,一般是写作“臊子”。陕西有臊子面,这个臊子指的就是切好的肉丁炸出来以后,用作面的浇头。特别是岐山臊子面,太有名了,全国各地都有写着岐山臊子面的小店。贵阳街头的脆哨,还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简直和铜鼓一样常见。
说到铜鼓,贵阳街头经常看到铜鼓的形象,因为贵阳有铜鼓山、铜鼓滩、铜鼓广场,还有贵阳古八景之一叫“铜鼓遗爱”。在城东水口寺,有一座植被丰茂地势险峻的高山,就是铜鼓山,此山有个“仙人洞”,洞深约二十米。因洞中通风很好,空气对流,人站在洞口,可闻洞中有嗡嗡之声。民间传说,当年诸葛亮南征时,把铜鼓藏于洞中,于是洞中能发出声音。故而,此洞又名铜鼓洞。明代正德三年,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驿,曾应邀来贵阳书院讲学,到过此洞游览。
这天下午,我在南巷咖啡馆里坐着的时候,就接到作家彭澎的电话,说要带几个作家一起去铜鼓山走走。我对着菜单犹豫不定,有心想要试一下折耳根咖啡的怪异之味,又觉得可能会错过“铜鼓遗爱”。不过我很快说服自己,既来之,则安之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世上事,何来错过一说。该遇上的,终归会遇上。何况,我还想在这里再喝一杯湄潭翠芽。菜单上有这一道茶。我以前听说过湄潭翠芽,《茶经》上说湄潭出茶,“黔中生思州、播州、费州、夷州……往往得之,其味极佳”,《太平寰宇记》也说“夷州土产茶”,现在的湄潭县域,就属当时的夷州境内。这时候,咖啡馆姑娘说,这个时候店里没有湄潭翠芽的新茶,只有老茶。绿茶只有当年新茶才可一喝,老茶就没有意思,遂打消了念头。世上的茶也是这样,该遇上的茶,以后终究会遇上,不必着急。
此番到贵州,是参加黔东南州雷山县的苗年暨鼓藏节活动。在雷山县城,不仅有铜鼓广场,也有很多有特色的食物,我们步行前往铜鼓广场的路上,见到好多家牛瘪汤饭店。大大的招牌,大大的字。牛瘪我以前知道,当地人称之为“百草汤”,实际上就是牛的胃及小肠里未完全消化的食物,煮出来,是一锅浑浊的绿色浓汤。
一群天南海北的作家们,在喝牛瘪火锅汤前,集体对着摄像头兴奋地喊:“遇见贵州,人间烟火抚人心”。吃吃喝喝,是真正抚慰人心的事。在苗年的庆祝活动中,有一项重要的活动,就是吃饭,当地人一般是长桌宴。我们在铜鼓广场也吃长桌宴。夜深时候,仍有三五成群的当地人,还在长桌宴上酣饮,叫人羡慕不已,也感动不已。
就在这样的长桌宴上,店家也给我们上了一碗新鲜的折耳根。其他客人敬而远之,唯我一个人慢慢地品尝,居然吃了半碗。
折耳根炒腊肉,真是可口的一道菜。腊肉很香,折耳根甜中带些软糯,比生吃的时候味道清淡。这道菜下酒真是好。有一个晚上,彭澎兄带领一大群作家吃饭,王祥夫、张立军、玄青花、刘欠欠、李世成、童子、山叶、离离等人,我们一边举杯,一边大啖腊肉折耳根。
我忽然悟到,这一年中,我所吃到的折耳根,几乎都是在贵州。对我来说,这也算是属于贵州的独一份的记忆。